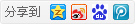文化消费主义时代,精英和平民都是资本的囚徒
时间:2017-03-29 14:32:11 来源:ifeng.com
[导读]导语:近日,随着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商业娱乐入侵文化的恐慌也再次蔓延。诗词大会被批评者们指认为异化了的“背诗大会”,陈粒演唱的“青春版”红楼梦主题曲《戏台》因“婊子”、“给钱就能睡”等字眼引起了口诛笔伐,《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朗读类节目也因“消费文化的情感类节目”而饱受诟病。
导语:近日,随着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商业娱乐入侵文化的恐慌也再次蔓延。诗词大会被批评者们指认为异化了的“背诗大会”,陈粒演唱的“青春版”红楼梦主题曲《戏台》因“婊子”、“给钱就能睡”等字眼引起了口诛笔伐,《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朗读类节目也因“消费文化的情感类节目”而饱受诟病。但评论人卢南峰指出,所谓商业入侵文化并非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鲜事,这种恐慌实际上贯穿了20世纪后半期大众媒介高歌猛进的整个历程。
究其原因,与平民文化相伴而生的商业文化长期以来都被默认为大众领域的文化消费,所以当它开始消费所谓精英文化领域内的诗词、红楼时才会引发惊诧和恐慌。但商业文化本身就是无本质内容的,可以与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任何一方媾和,将两者合并为简单易懂可以贩卖的东西,兜售着廉价而暂时的快感。因此,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框架下,真实的忧虑并不是精英与平民的对立,而是文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势不可挡。

冯其庸
2017年1月22日,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逝世。2016年12月7日,微信公号“新世相”发布青春版《红楼梦》的宣传文案,成为朋友圈刷屏热点,关于“亵渎经典”的口诛笔伐也纷至沓来。2017年2月25日,青春版《红楼梦》主题曲、陈粒演唱的《戏台》发布,延宕了自去年十二月开始的这场口水官司。
时代喜欢互文的修辞手法,当它想要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给出的隐喻总是成双成对,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冯其庸和新世相作为一对互文,隐喻了商业文化汹涌而来,“昨日的世界”分崩离析,文学经典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被收编、拆解、重构、贩卖,让人生发“时代已经变了”的感慨。
然而,新世相们给冯其庸们带来的挑战,《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节目带来的“文化经典如何普及”的问题,并不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鲜事,“商业娱乐入侵文化”的恐慌实际上贯穿了20世纪后半期大众媒介高歌猛进的整个历程。
三军混战,而非两军对垒
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不断降低“文化”的门槛,削弱精英对于文化的垄断。印刷术的大规模普及,扩大了识字人群;无线电技术带来了广播时代,BBC最早还试图将其作为精英文化的“布道台”,但大洋彼岸商业广播的出现很快实现大众化与娱乐化;而基于摄影术的电影,成为工人阶级最廉价的娱乐方式。

Civilization
上世纪六十年代,电视普及引发的媒介革命,为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提供了新的战场。1968年,BBC推出了史上最具有野心的系列纪录片《文明》(Civilization),由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解说,13个小时的影像试图用欧洲传统艺术对抗由美国入侵的商业性流行文化,从流行中拯救日渐式微的“文明”。巨额投资而精美绝伦的《文明》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将欧洲传统艺术拉回了人们的视野。克拉克爵士在解说中不无倨傲地宣称:“我相信,秩序优于混乱,创造强于毁灭。首先,我相信,神把智慧赋予特定人群,我珍视一个可以让这种人生存发展的社会。”

法国五月革命风暴
而一个作为互文的隐喻是,就在克拉克爵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漫步卢浮宫外,为《文明》拍摄素材的同一时间,法国正爆发“五月风暴”,国家滑向内战的边缘,学生们占领学校、筑起街垒、展开巷战,在城市的围墙上到处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对僵化的现存体制发起了冲击。战后的黄金时代终结了,五月风暴成为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一个顶点。中产阶级年轻人们试图用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和东方神秘主义,挣脱一切传统与主流文化的束缚。而从整个六十年代的反叛氛围看来,克拉克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是如此不合时宜,仿佛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冲锋。
克拉克认为“文明”是维系于“特定人群”,而这位爵士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大众社会。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工人阶级兴起,大众民主出现,群众进入了历史。一方面,这些人不再对高高在上的精英顶礼膜拜,在精英文化之外自创了一套粗陋却充满生命力的工人文化或平民文化;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大众社会文化需求的激增,资本也在努力迎合非精英的口味,创造了一套基于盈利目的的商业文化或流行文化。 对于克拉克而言,平民文化和商业文化似乎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社会下层是如此容易被粗陋恶俗的商业文化所俘获,他们被动、轻信和乐于偶像崇拜,威胁着“真正的”文化。
与贵族克拉克相比,同时代的雷蒙德·威廉斯,更能把握平民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区别。威廉斯出身工人家庭而进入剑桥,成为英国精英文化圈的一个“闯入者”,他一生都致力于从精英手中解救对“文化”的狭隘定义,发掘那些被精英所遮蔽和鄙薄的平民文化。在他看来,文化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那么不仅精英的歌剧、画展和交际舞会是文化,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一样可以是文化,并且是精致而非残缺的文化。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大众媒介中的权力不平等,精英在说,平民只有听的份,而精英们总是在想象中先制造出一个盲从轻信的“大众”,然后再撸起袖子批判这个“大众”。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三角关系。精英文化将平民文化与商业文化都视为野蛮的威胁,而自己则努力维系千百年来弥足珍贵的文化标准;平民文化,认为精英控制大众媒介掌握话语权,更进一步批判商业文化压根就是资本主义麻痹人民、消解反抗的统治工具;商业文化则没有那么多道德预设,无论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都可以成为我的素材和内容,实现商业成功与资本增殖。
在思考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我们常常将其视作高雅与通俗之间的两军对垒,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分庭抗礼,但这种二元对立有过多混淆不清的地方,精英文化、平民文化与商业文化三军混战的理想模式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问题。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我们暂且搁下对垒与混战的故事,将镜头拉回到中国。
中国自初,政治与文化就水乳交融,难舍难分,魏晋时代还是门阀世家,贵族遗风,到了隋唐以降,承平时代的统治集团逐渐变成了科举体制培养出来的一帮文人,他们在朝辅佐君主,在野表率乡里,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有梯度的政治统治和文化领导集团。最关键的是,尽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民谣是过于理想化了,但这一集团确实是相对开放与流动的,也就成为汇聚社会各个阶层及其文化意识的流动管道,在这个管道里的人是能相互沟通的,贵为宰相的人也能够理解农桑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平民主义传统,无怪梁漱溟说中国古代只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对立”。
战国宋玉《对楚王问》,很早就点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差别,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并不认为“阳春白雪”有资格鄙薄“下里巴人”。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并不对抗,白居易作诗追求通俗浅白,“每作诗,令老妪解之”,只有老太婆能听懂的才是好诗;柳永用俚词俗语,“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更遑论勾栏瓦肆里的宋元戏曲与明清小说……而这些流传甚广的传说都烙印进了我们的文化心灵,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意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鄙视链不存在,与文学艺术的平民传统不同的是,作为统治学说的儒学又是高度政治化的,并不被视为文艺的一部分,“道学家”要维系着“道统”和社会风气,如贾政不许贾宝玉读那些淫词艳曲,这是出于政治与道德的考量,然而贾宝玉还是要偷偷去读,对“不正经“的文化并没有品质上的鄙薄。从总体上而言,中国传统较少受到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藩篱的搅扰。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打碎了正统道学的蛮横控制,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勃兴,平民传统进一步深化,“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成为了社会主流,就更无高雅与通俗之间的文化战争了。
所以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与其说是两军对垒,不如说是两军会师。然而近年来,“第三军”,也就是前述的商业文化异军突起,开始迅速建立起庞大的文化消费体系,将所有的文化事态都卷入其中。

中国诗词大会武亦姝
《中国诗词大会》,“现代才女”武亦姝走红,支持者讲述的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舞台尝试,让诗词从尘封的语文课本里面复活,带来的是古典诗词的大众化,老少都爱看文化普及节目,总比去看偶像剧和真人秀强;而批判者讲述的故事是最讲求灵性与体悟的诗歌变成了“比谁背得多”的文化噱头,赚足了收视率,而诗歌所承载的思想精神内核都不见了,只剩下了作为花哨的娱乐形式,对于古典诗歌未必是一件好事。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框架下,真实的忧虑并不是精英与平民的对立,而是文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问题。
精英文化、平民文化与商业文化三者本身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叠的,而围绕它们的讨论也不作区分,交杂不清。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作为“搅局者”的商业文化到底为何物?
广告和资本主义白日梦
让我们回到克拉克爵士。同样与克拉克的《文明》能形成互文,揭示这场文化战争的是,1972年约翰·伯格针锋相对的BBC纪录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在这部片子的开头,头发蓬乱、眼神飘忽、面部沟壑纵横的约翰·伯格用裁纸刀从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与马尔斯》切割下维纳斯的头像(当然不是真品),然后下一个镜头是维纳斯头像在印刷机里被批量生产出来。这一破坏名画的举动似乎是对克拉克之流的老古董的嘲讽。

在《观看之道》中,伯格用刀划开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画像。
伯格想说的是,一幅艺术品挂在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书房里,观看这幅画需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和视角,暗暗告诉观看者“你是世界的中心”。而机器则复制了这些视角,将克拉克引以为傲的欧洲传统艺术“去神秘化”,抹去围绕在它周身虚幻的权威,走向了民主化。克拉克之流之所以对传统艺术怀有“虚伪的虔诚”,不过是想让艺术原件在丧失提供“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之后,还能保有其权威和市场价值,“艺术使不平等变得高贵”。
但是,机械复制在带来了艺术的去神秘化与民主化的同时,也催生了大众媒介里的商业文化。在伯格看来,这些商业文化与“独一无二”的油画,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编织白日梦欺罔被统治者的两种工具。不同的是,油画时代,艺术品的目的在于宣示主人已经享受到的一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商业文化产品和广告,目的是让观众对自己现有的生活产生不满,从而产生消费冲动,幻想藉此改善生活。“资本主义迫使受它剥削的广大群众将自身利益规定得狭隘无比,以维持它的生存。”这也是新世相被指斥的地方,它通过拟仿拥有名家油画般的情怀、格调与身份感,为都市中生活重压之下的年轻人制造逃离的假象,满足他们对有闲阶级消费与生活的暂时满足。
相较于持平民立场的伯格,二战时期流落美国,亲眼见过强大的商业文化,持精英立场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对这一套商业文化体制发起了激烈的批判。在《文化工业》的这个文本里,他们以晦暗的笔调勾勒这个商业文化的图景: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文化产品像工业流水线一样变得标准化和程式化,批量生产,机械复制,同时这些文化产品也喂养了受众的单一品味,人们在消费这些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融进了这套工业体系里。它生产这样标准的产品,培养了你标准的口味,而你标准的口味,则进一步促进它标准的生产,这个循环最终完成了人的标准化。整个统治体系对你的控制,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世界的彻底殖民,消解了你所有的反抗意识,心甘情愿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环节。
商业文化从内容上空无一物,它是一种文化的组织形式,可以与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任何一方媾和,同时侵入两种文化的肌体,文化工业破坏了严肃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界限,将两者合并为简单易懂可以贩卖的东西,兜售着廉价而暂时的快感。
而今天的中国人或许愈发能理解他们的耸听危言,这个听上去毛骨悚然的画面就在我们生活中悄然运行,渐渐地我们发现,电视电脑荧屏上不断播送的偶像剧,微信公号里各种雷同的营销号,正在从精神层面使我们的文化品味开始趋同,借由文化工业的布道,北上广深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我们在朋友圈里分享着相似的符号,旅行、美食、摄影、咖啡厅、马拉松……传媒桎梏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大都市平台、机遇、人脉、眼界、生活方式的神话被建立,小城小镇乡村生活成了落后封闭的符号,回不去的是荒颓的故乡。

青春版红楼梦
当人们以为某种符号,比如可以拿在手上拍照的《红楼梦》是一种品味的象征的时候,它本质目的却不过是诱引你去消费,给你制造你在这个程式化的文化工业中“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错觉。而你真正想要的,或许并不是“与众不同”,彻底的“与众不同”让你感到害怕,你需要的是与他人相比细微的优越感,毕竟在这个文化工业中,这种“细微”也成为一种奢侈,所以你要为这种“细微”掏额外的钱。
卢南峰,北京大学新闻学硕士在读,研究兴趣是青年网络群体的政治文化意识,(伪)学术概念发明爱好者。
声明:i天津视窗登载此文出于传送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网友参考,如有侵权,请与本站客服联系。信息纠错: QQ:1296956562 邮箱:12969565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