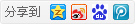新版《美女与野兽》是升级版的女权主义表达?
时间:2017-03-29 14:29:12 来源:澎湃新闻网
[导读]艾玛·沃特森出演了《美女与野兽》,让这部电影及其童话原著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成为了一个热闹的话题。著名女权主义公众号“女权之声”几日前发布《:基因里的女权主义》一文,追溯了这一童话诞生时对男权反抗的意味,后来的迪士尼版本又创造了在众多被保护的迪士尼公主外,独立自由的女权公主。此文认为,艾玛·沃特森的这一真人版本更是女权主义的升级版。
艾玛·沃特森出演了《美女与野兽》,让这部电影及其童话原著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成为了一个热闹的话题。著名女权主义公众号“女权之声”几日前发布《<美女与野兽>:基因里的女权主义》一文,追溯了这一童话诞生时对男权反抗的意味,后来的迪士尼版本又创造了在众多被保护的迪士尼公主外,独立自由的女权公主。此文认为,艾玛·沃特森的这一真人版本更是女权主义的升级版。然而,倘若在17世纪诞生之初,《美女与野兽》尚有一定的对父权的批判意味,到了今天,回归城堡的公主如何能成为当代女性的表达?它或许仅仅是制造了中产阶级的上升幻象,以完成文化工业在消费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驯化功能。
从1756年博蒙夫人构思创作《美女与野兽》故事以来,这个脱胎于民间故事类型体系里“野兽新郎型”故事的经典,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写,可谓文学和电影改编史上的宠儿,亦被认为从诞生起便蕴含着女权主义的基因。其中1991年迪士尼动画版的《美女与野兽》更是被调侃为“会逼得坚持男性至上主义的老迪士尼本人在坟墓里都不得安宁”的大胆作品。不过最初的惊喜过后,也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这部影片中的“女权”是否流于表面。
《美女与野兽》的性别与阶层血统
专注于考察儿童与文化工业关系的著名儿童文学研究者杰克·齐普斯曾引用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中关于“体制化”的说法,提醒人们注意消费社会中童话的文学与电影版本改编对接受者的驯化功能。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一提齐普斯在《童话的起源》一文中梳理过的《美女与野兽》故事的前世今生。齐普斯在文中分析了该故事产生的法国沙龙女性文化背景。17世纪时,贵族妇女开始发现男性主导的评价体系中自身的不利地位、质疑评价的不公,在借童话故事进行的自我描绘中对这些评价作出了回应,但她们又并不想改变既有的家庭与社会结构,于是这些贵族女性在故事中尽可能温柔地展示阴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母性的力量(这一点下文还将讨论,而从经典版故事的主插画和海报中也能看出——往往是美女爱怜地凝视、抚慰着怀中奄奄一息野兽,动作神态与西方油画中著名的“圣母哀悼基督”主题十分吻合)。

剧照
早期《美女与野兽》中女主人公被强调的美德是“顺从”与“自我牺牲”,而顺从与牺牲的对象从父亲过渡到“丈夫”,同时也昭示着女性的“成人化”。因此,经典版《美女与野兽》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妥协性产物,女主人公对父亲有着俄狄浦斯情结,在一些脚本中甚至存在明显的乱伦情节。对于女主而言,野兽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父亲,而在最后女主必然得到一座华丽而舒适的城堡、相当符合主流审美的王子作为奖励;在德维尔纳芙夫人的版本中女主因为自愧商人出身决定离开恢复“完美”的高贵王子,而最后则被证明商人只是她的养父,beauty原来是另一位国王的女儿。美德不单与美貌,也必须与出身息息相关,性别权力博弈以及中产阶级的艰难上升之路——这是《美女与野兽》故事原有的血统。
艾玛·沃特森版《美女与野兽》
说回今天的电影,女主人公显然因为阅读而不再满足于充满陈规和偏见的乡镇,渴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不再遵守誓约,她中途决意出逃;不再以牺牲姿态去换取父亲而是拯救不成不得已选择交易,这些都比经典版故事中的设定要更加接近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自由、平等的理念。
然而可惜的是,和真人版《灰姑娘》一样,时隔二十多年后的这部真人版《美女与野兽》前进之处少得可怜。整个故事里保留着的性别与阶层偏好血统如果在1991年动画版上映时不为人所多加追究尚可体谅,今时今日我们在将其定位为父权价值观的公开批判者时则需要更加慎重才是。


插图
稍稍回想便知:影片中的野兽比村民们究竟强在哪里呢?他很富有,只要他愿意他也可以很懂贵族的礼仪,他还有藏书——但我们自始至终都无法从片中得知这些藏书他到底阅读过多少,这位野兽多大程度上获得了书籍所代表的超功利和智慧世界的准入凭证呢?他甚至需要贝尔去教会他人类基本的用餐礼节——或许他是变为野兽后“放弃”了文明社会的用餐形式,但如果从童话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他甚至可能从未曾真正习得这些基本文明。如前文所说,在早期的《美女与野兽》故事版本里,美女的文明与野兽的原始野蛮正是故事讲述者——沙龙贵族妇女设置的基本人物矛盾,她们暗示男性即使出身高贵也是需要女性教化真正文明的野兽——这一设定在18世纪时还具有早期的女权意义,我们但愿当下的男性观众依旧不会觉得这个假设其实挺伤人;而贝尔高歌等待人来“拯救”自己和早期唱着同样拯救之歌的白雪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一出城堡的大门就要遭遇饿狼又是什么设置呢?我从茶壶夫人凝望出逃贝尔的眼神里仿佛看到了老式《小红帽》故事里焦虑而恐惧的母亲的双眼——别出门宝贝儿,外面狼多。
齐普斯在评价1987年朗恩·考斯洛制作的现代电视剧版《美女与野兽》时所说的“其中不乏积极的因素,比如不被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而阻碍的女性和试图读懂女性灵魂的别样男性,然而男女主人公被理想化为一对有着神秘联系的人物。而且男主角始终代表着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不可能在乡镇街道上实现的更高的理想”同样适用于迪士尼版《美女与野兽》。不过,后者事实上更加保守,影片在对女性命运的书写中不敢释放更多的想象力。关于幸福的想象,仍是黄金的宫殿和符合大众审美长相的王子,甚至忘了这个女主人公最开始的宣言——山坡上天空下、外面的世界——贝尔哪怕真的走出过这个树林子围绕的乡镇和城堡然后反悔也好啊。哦她出来过,只不过巴黎被设置成一片暗夜无人区和只代表回忆的瘟疫之乡——就像树林里的狼一样。
与经典版类似的问题是:贝尔在家中和在城堡中有什么不一样,如果阅读让她对乡镇的陈规和狭隘见识产生不满,那么影片中的城堡在这方面又呈现出怎样的优越性了呢?“她那并不见得崭新的‘新’生活将会是富有而舒适的”,从前如果家务劳动产生的经济价值还能使她不算真正的“啃老族”,那么成为王妃以后呢——毕竟影片除了野兽让贝尔离开时说“她应该有自由”这一次表态之外,再没有任何能让人作出积极推测的暗示了。这里“自由”的指代也很含混,包不包括她也能享有婚后不顾王室传统出门工作、探索世界的“自由”呢?根据现有情节,完全无法预知。她的勇敢和善良得到了一个华丽舒适生活的安抚,全场人物无师自通地跳起了王室之舞,人人柜子里仿佛都藏着一件贵族制式的大礼服,不过贵族暂时性地擦掉了大浓妆,美声改成了通俗唱法,深夜闭门自嗨改成了白日宫廷平民大联欢——中产阶级或成最后赢家(也只是“或”),老迪士尼式处理永不过时。

插图
消费社会中童话的改编对大众的驯化
作为文学的爱好和研究者,我当然知道“城堡宫殿”和“王子”并不只意味着财富、权力和大众情人,它们是广义上的人类“欲求”的符号,任何层面任何方向上的欲求。这种义涵上的空间要求我们对文学宽容——它很可能为一不小心就走向偏狭、非左即右的人类保留了最后的转圜余地;然而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隐喻,其各项喻体符号本身亦是意义的合集,这些符码义涵流动却并非毫无限制,“宫殿”和“王子”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联想意义群,而童话一定程度上是顺承、利用而并非颠覆这些稳定义涵来传达意义。正因为这些隐喻赖以构成的桥梁是反映社会文化的镜子,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时时检视、反思我们的思维桥接方式。在明知历史上我们的先辈妇女们金丝雀般的生活地位时,我无法毫无阻碍地把这部影片中的城堡宫殿和符合大众审美的王子这一奖励与人类世界抽象意义上的“欲求”和“美好”作同义替换。

配图
彼得·比格尔曾把艺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宗教艺术、宫廷艺术和资产阶级艺术。越往后发展,创作的功能越淡化偶像崇拜而趋向自我意识的展现,艺术的生产和接受者也从集体向个体发展。从生产者来看,迪士尼作为团队历经百年屹立不倒,作为把准美国最主流大众文化价值观脉搏的美国荧幕保守系创作/生产者,自然怎么也不能算是个人化的创作;从受众角度来看,相对稳固或者说规模的受众集体形成,尽管影片似乎强调的是“自我意识”的发展,但其作为商业电影的运作形式一样也不少,粉丝的追捧、周边的热卖也让人很难说观影会是一次基本只涉私人的消化行为。如此种种都反映出消费社会里大型文化工厂输出的产品,尤其是对经典文本的商业改写吊诡地染上了昔时“宗教艺术”才具有的特征,童话被新一轮制序化、神话化。在对女主的大规模赞赏中,但愿人们不会忘记其实他们本可以有更多选择。

声明:i天津视窗登载此文出于传送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网友参考,如有侵权,请与本站客服联系。信息纠错: QQ:1296956562 邮箱:12969565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