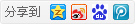这些老画家在掀起中国画革新之前,曾积极地向日本学习
时间:2016-12-01 19:28:28 来源:澎湃新闻网
[导读]在1905-1937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画家对日本画坛的了解和借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广得多,所受影响既非限于一家一派,更非单一的技法学习,而是大多能融合多种元素,尽量综合地感知日本画坛的新气息。摹借成为他们中国画革新探索的动因和重要凭借,如果没有留日经历和对“日本经验”的摹借,这些画家的中国画革新探索将是难以想象的。
在1905-1937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画家对日本画坛的了解和借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广得多,所受影响既非限于一家一派,更非单一的技法学习,而是大多能融合多种元素,尽量综合地感知日本画坛的新气息。摹借成为他们中国画革新探索的动因和重要凭借,如果没有留日经历和对“日本经验”的摹借,这些画家的中国画革新探索将是难以想象的。

山本梅庄《骷髅》

高剑父《白骨犹深国难悲》
古今中外的画家均离不开对别人的学习,这种学习大致有“摹”与“借”两种方式,前者偏于亦步亦趋的临摹,易于辨认,比较“明”;后者偏于借鉴后的转化,与其“来源”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相似性和变异性,更因所“借”往往并非一种,“转化”出来的结果较为复杂,而相对较“隐”。
自20世纪初开始“东奔西突”地向“东洋”、“西洋”学习以来,关于摹借,我们大致拥有了对内与对外的两种态度。对内,我们依旧延续着历来对“临”、“摹”、“仿”、“抚”的不避讳态度,甚至常见以“笔笔有来历”而标榜脉系纯正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仰赖的是自为的评价体系,其核心是笔墨的质量,而笔墨的质量除了技巧的娴熟之外,更多的是表象背后以文化修养为支撑的气息、格调、韵味以及精神、个性甚至品德等诸种因素,即“临”、“摹”、“仿”、“抚”的仅仅是表象或笔墨的技巧、样态,并非风格的全部,决定风格的那些关键因素则永远是独特而无法被取代的。
对外,又大致呈现出两种倾向,即对挪借“东洋”(日本)的否定倾向,和对挪借“西洋”(欧美)的肯定倾向。其中,中国画对“西洋”的借鉴无非是与“写实”相关的透视、明暗,和嫁接西式“写意”、“抽象”与写意中国画的努力,相对较为单纯;而对日本的借鉴情况则较为复杂,既包括与传统中国画渊源颇深的南画体系,也有偏于装饰、甜美、雅致的日本画体系,更有所谓“二手西方”一脉,总之,日本画坛东西洋融合与杂处的多元状态直接造成了中国画家“摹借”上的多元。

寺崎广业《长城之夕》

陈树人《长城暮鸦》
关于“对外”的摹借,一方面,我们对发掘近于抄袭的“摹”的史料怀有极大的期待,因为它们能确凿地被运用于研究,但即便我们终有一天可以将所有确凿的“抄袭”蒐集齐备,也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多么可观的存在,因为它毕竟不属于常态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借”,情况非常复杂,每一种具体的“借”都需要在史料基础上严谨论证方可确认。
白谦慎在其著述《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关于“影响”的论述值得参考。“影响”或“摹借”,通常是在我们看到了绘画形态上的某些相似特征后引发的联想、追索乃至论证,而“相似”大致可以由四种原因造成:一、直接的师承和有意识的临摹。这个原因最好理解和证实,不赘述。二、潜移默化的视觉影响。即相同的视觉环境和审美参照之下,会出现风格趋同的现象,这也是所谓时代风格、地域风格、画派等等的成因之一。它与直接的取法是有区别的,有时候相近的风格未必就是“摹”来的,或者说,“潜移默化”这一难以论证的因素是在整个绘画史上始终存在的;三、相同的渊源。即A与B相似,未必就一定说明A与B有直接的影响关系,很可能他们均源于C或者更为“曲折”地源于D,这样的例子在美术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四、巧合。即往往两个完全不可能发生关联的个体,在绘画风格上产生了近似,这种情况也为数不少。
总之,“摹借”也好,“影响”也罢,均非我们能用已有的美术史认知“想当然”地得来,我们既不能将存在相似性的个体轻易从历史的上下文逻辑中摘出,简单并列,强求关联,也要避免类似“前人一定影响了后人”、“主流一定影响了非主流”、“官方一定影响了民间”之类的想当然判断。与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关于摹借,也需要避免宏大叙事和主观先行,同样需要从材料出发,审慎分析每一种摹借的具体性和独特性,有多少史料便做多大的文章,史料不足,便索性付之阙如,方不失为一种正确的学术态度。

小林古径《鹤与火鸡》

方人定《后园》
对于此次展览无法回避的摹借问题,我们在有限条件下做了尽可能的梳理,大致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从已有研究成果中汇集十一家对日本的摹借情况,再经少量增补和修正,以列表的方式呈现,其中包括能一一对应的作品和仅能列出名字的画家;其次是按文索图,尽量找到对应作品的实图;第三,尽量找到所摹借的日本画家的作品作为辅助说明,但因我们很难看到每位日本画家的全部面貌,所以在选择上难以做到典型和准确;第四,尝试从各种渠道的图像资源中,寻找“相似”,意在提示“影响”的可能性,但这部分内容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也只是诱于图像的直观性,希望将图像来源的搜寻范围适度开放,拓展思路和视野——因为对可能性的探讨历来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
我们大致能找到以下相似度较高的对应作品,即高剑父的《火烧阿房宫》与木村武山的《阿房劫火》,高剑父的《风雨骅骝》与桥本关雪的《意马心猿》,高剑父的《昆仑雨后》与山元春举的《寒村暮雪》,高剑父的《白骨犹深国难悲》与山本梅庄的《骷髅》,高奇峰的《白马》与桥本关雪的《意马心猿》,陈树人的《落机残雪》与山元春举的《落矶山之雪》,陈树人的《芦雁》与望月玉泉的《芦雁》,陈树人的《跃鲤》与今尾景年的《跃鲤》,陈树人的《长城暮鸦》与寺崎广业的《长城之夕》,陈之佛的《芦花双雁》与伊藤若冲的《芦雁》,方人定的《闲日》与川崎小虎的《黑衣的支那美人》,方人定的《后园》与小林古径的《鹤与火鸡》和傅抱石的《屈原》与横山大观的《屈原》等。

横山大观《屈原》

傅抱石《屈原》
此外,在我们有限的查找中,发现高剑父的《乌贼》与竹内栖凤的《宿鸭宿鸦》,在笔墨的氤氲气氛上有类似。陈树人作品在疏朗、明快、清新的气息上接近菱田春草;他的《蒲堂雨过》、《花溪细雨》、《冰天立马》与山元春举的《春夏秋冬》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他的桂林写生系列棱角分明的短笔折带皴又似山元春举画法的变体。陈之佛的雅洁趣味、装饰感乃至花鸟形象本身,很有可能与酒井抱一的《十二月花鸟图》、尾形光琳的《红梅白梅》和伊藤若冲的《梅花群鹤》,或今尾景年的诸如《月下芙蓉鸳鸯图》和《白桃鸚哥图·牡丹小禽》等等,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从日本画人物画中寻求突破的方人定,其早期女性题材人物画之姿情,显然源自日本仕女题材作品,如果将其此类作品与镝木清方的《薄雪》、三木翠山的《维新之花》或横山大观的《观音》等相并置的话,似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关联性;而方氏《到田间去》一类追求稚拙感和原始风的作品,显然并非直接源自高更,日本画坛如加纳三乐辉的《海之市日》和《南岛女人》一类的作品,仿佛更应该是方氏借取的依据。丰子恺对竹久梦二的借取较为单一和明确,但我们发现,丰氏少有“摹”,而主要是“借”,我们既能明确丰氏作品与竹久梦二作品在情调和神韵方面的关联,也能同样明确感知丰氏巧妙而超凡的转化能力。傅抱石对日本画坛的借取较为多面:其《琵琶行》有着与桥本关雪《琵琶行》类似的构图,此外,日本人物故实画中对中国题材的涉猎,也带给他天然的吸引力,直接促成他日后对人物故实画的诸多尝试;其《石勒问道》与桥本关雪的《访隐》,构图近似,但笔法差异颇大;其《竹林七贤》与桥本关雪的《竹林烟月》,在环境气氛尤其是光影感、空气感的营造上,似也能建立关联;傅氏在笔墨质感及章法上与平福百穗最具相似性,这在后者的《清江捕鱼》和《坚田的一休》等作品中均不难看出;傅氏的仕女形象也有着明显的“日本”特征,如《山鬼》与川崎小虎的《佛观中将姬》、村上华岳的《日高河清姬图》等,在仙、鬼气息上有相似性,而这种气息为传统中国画所少见;我们甚至也能在傅氏《芭蕉叶绿上娥眉》一类仕女形象,与镝木清方《薄雪》中黑衣女子的姿情之间,建立起某种想象。黎雄才的《潇湘夜雨图》、《富士山之夏》、《风雨归舟》的没骨渲染手法以及造型本身,很可能与菱田春草的《渡船》或“朦胧体”横山大观之《东山》、《生之流转》等有关,而黎氏保持了一生的湿重墨气和雄强、飞扬的硬笔散锋,又与今尾景年的《风雨归渔图》很类似。
上述每一种“相似”均未经考证,仅仅是依据图像本身所作的一番罗列,其中的某些“对应”极有可能不成立或“对应”者是风格相似的其他画家、作品——相信无论是山元春举、菱田春草、竹内栖凤、横山大观、镝木清方还是平福百穗等等,在日本画坛均应有不少追随者,而摹借未必一定限于对一流大家的学习,事实上,留日画家们的直接日本老师很少一流大家,但却不乏一流大家的弟子或某流派成员,他们大多未能留名于美术史,但不意味着在当时不具备对周边的影响力。与其说我们寻找的是与具体画家或作品的对应关系,不如说我们是在梳理摹借的n种倾向或风格。

伊藤若冲《梅花群鹤》

陈之佛《梅鹤迎春》
此外,西画出身的朱屺瞻、关良和丁衍庸,根基是以黑田清辉为代表的日本写实西画和在日本观摩到的西方现代派,虽然并无类似上述画家的“摹借”实例,转向中国画也相对较晚,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手”西画给了他们更符合东方审美的造型基础和转向中国画的自由度,他们的摹借方式和大跨度的转化力,作为极其独特的摹借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发现,在1905-1937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画家对日本画坛的了解和借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广得多,所受影响既非限于一家一派,更非单一的技法学习,而是大多能融合多种元素,尽量综合地感知日本画坛的新气息。同时,他们的摹借也存在着与日本画坛的机缘差异,即必然性之中有偶然性。但无论必然还是偶然,均成为他们中国画革新探索的动因和重要凭借。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留日经历和对“日本经验”的摹借,这些画家的中国画革新探索将是难以想象的。
历史地看,中国画家向日本画坛如此成规模地主动、积极的“摹借”,是空前的,但并非是绝后的。事实上,时隔约半个世纪的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画坛再度兴起了摹借日本的潮流,甚至“抄袭”的现象也并不鲜见,但不仅更偏于技巧层面,且摹借面貌也欠缺多样,大致可以概括为较为单一的工笔潮流。可以说,近三十年来貌似“繁盛”、实则单调的中国工笔画坛所遍布的“制作”风气,与“日本”有关。同为“摹借”,何以半个世纪间会有如此大的落差呢?
“摹借”貌似简单,实则是个极为重要的能力,如何“摹借”甚至是美术史的重要课题:当吴昌硕大写意花鸟“横行”之时,为何只有齐白石、潘天寿学而能出?在齐白石为数众多的弟子中,为何只有从不摹其一笔的李可染能独得其神髓?同样学习“日本”,为何既可以转化得异彩纷呈,有时却却乏善可陈?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见前人,用以比照今人。在“摹借”问题上,摹借了什么或许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摹借”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有价值的永恒话题。
苏文惠、林夏瀚提供诸多建议与帮助,在此申谢。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标题系编者所拟,本文原题为《关于摹借》,发表有删节,原文附表与注释未收录。

声明:i天津视窗登载此文出于传送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网友参考,如有侵权,请与本站客服联系。信息纠错: QQ:1296956562 邮箱:1296956562@qq.com